
访谈时间:2015年7月21日
访谈地点:西北师范大学
一、如何正视并雕刻民族苦难
张晓琴:杨老师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您的创作自始至终充满一种巨大的力量,敢于正视20世纪这个国家的民族苦难,并且以文字雕刻出来,这是您创作中最闪光的一部分,是什么样的原因使您将笔力挺向民族苦难?您创作的初衷是什么?
杨显惠: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饥饿是我成长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体验。从上小学到初中,一直饿肚子,这个饥饿是忘不了的。虽然我没有在农村待过,可是城市里的人也是吃不饱的。当时城市的每一家门口不断的有从乡下跑来要饭的,一个进来走了过一会又一个进来走了,能够跑出来要饭的人都是有一定勇气的,很多没有要饭的人饿死在乡村,这个事情我们都非常清楚。我是1965年主动申请上山下乡的,上山下乡时父亲不同意,我是从家里偷跑出来的。我也没有直接到农村,而是到生产建设兵团。在我的印象中,永远在饿肚子。在我们兵团,真正不饿肚子到70年代了,我们农场里面自己种的粮食够吃了,我们才不饿肚子了。可是这个时期,甘肃定西等地的人跑到我们兵团要饭的人还在继续。全国人民吃饱肚子是在土地承包的第二年,这一年开始大家就吃饱了。就是这些经历,包括“文化大革命”不正常的年代的经历促使我的写作发生了转变。在中学时期我就喜欢文学,所以我对上山下乡抱着一种非常乐观的态度,我觉得自己将来能当作家,无论是在哪里劳动,无非是向高尔基的童年一样经历一段艰苦,然后我一定会走向写作的道路。在上山下乡之前我就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张晓琴:您刚才提到您的家庭和父亲,家庭的文化背景有没有对您的创作产生什么影响?
杨显惠:基本没有,我基本不写个人的事情。
张晓琴:对,您确实很少写自己。饥饿体验本身是个人生活经验,而您把生活经验转变为生命经验,以“我手”写“他心”。
杨显惠:写自己无非就是自己偶尔去了哪一趟,知道了一些什么事,以自我的形式写一篇散文。
张晓琴:您的“命运三部曲”尤其是前两部,触及了当代历史上极度敏感的话题,这样的写作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您的勇气来自何处?
杨显惠:古话有一句,无欲则刚。
张晓琴:您的创作不得不让人想起阿多诺的那句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一些评论家把您称作“中国的索尔仁尼琴”,古拉格和奥斯维辛确实是人类苦难史上的标记,《夹边沟记事》的创作是否受到《古拉格群岛》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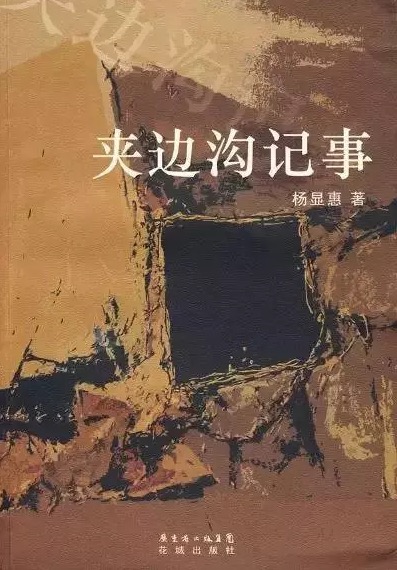
杨显惠:肯定有影响,《古拉格群岛》《日瓦格医生》这些作品我都是反复读过的,在我的心目当中,中国的作家全体加起来,其重量也不如《古拉格群岛》作家的重量。
张晓琴:当代中国作家往往被指认出与外国作家的相似性,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先锋小说作家往往被人称作“中国的博尔赫斯”、“中国的卡夫卡”,这样的判断往往是因其文学形式与外国作家的相似性,您与索尔仁尼琴的相似性是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的呢?或者说您本人是否愿意认可这种指认?
杨显惠:索尔仁尼琴敢于写一个民族的苦难,我觉得我也可以。至于写作的技术层面,我没有学习他的任何技巧。
张晓琴:您认为自己的创作与索尔仁尼琴的区别何在?
杨显惠:我是一粒沙子,索尔仁尼琴是一座大山,没有任何可比性。《古拉格群岛》不要说其内容,光是他的书的质量就是一大堆,很厚重,我只是写了那么一个薄薄的小册子。
张晓琴:索尔仁尼琴当然只是您精神资源中的一个,在他之外还有哪些作家、哲学家构成了您的精神资源?
杨显惠:我哲学著作读得很少。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实际上是肖洛霍夫,可是我的作品当中又没有肖洛霍夫的味道。俄罗斯文学对我的影响很深,俄罗斯文学厚重,场景宏大,作家对生活的热爱也是力透纸背的。高尔基是苏联时期的著名作家,实际上他在十月革命之前已经成名。他的作品不能完全归在第一个阶段——苏联文学阶段,他早期的作品是属于俄罗斯文学的。他的三部曲是经典,后期的高尔基已经贵族化了,成了斯大林的座上宾。
张晓琴:当代文学史上书写民族苦难的作品并不罕见,比如张贤亮、余华、严歌苓作品中的苦难就让人非常难忘,您认为您对苦难的雕刻和其他作家有何异同?
杨显惠:我认为张贤亮对中国文学有很大的贡献,他除了描述自己经历的生活和那个时代的苦难之外,文笔也非常漂亮,他是很有才气的一个人,我很钦佩他。严歌苓也一样,她有几本书写的很好。我们都在写同一个时代的事情,我们各自用自己的办法写,没有互相借鉴。我在写一个东西时,拒绝读同一题材的东西,我读张贤亮时,我才刚开始写作,张贤亮是我的老师。我读严歌苓的作品是在见到她本人之前,可是等到我去写这些东西时,我是不读他们的。
张晓琴:您雕刻苦难的终极意义是什么?
杨显惠:我希望整个社会都来反思我们历史当中的一些错误,我希望今后不再有这种事情出现。如果我们今天不把过去的事情进行反思,进行批评,那么我们将来可能还会走回头路。
二、如何面对采访与写作的伦理
张晓琴:您的“命运三部曲”中有些人的名字与现实中的一样,这确实给人一种非常“真实”的感觉,但是这种“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中往往会有一些与普遍的道德伦理相左的事情,比如发生在夹边沟右派身上的事情,从情感上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人同情的,但是从道德伦理上来说则是不合理的。我们当然明白道德伦理的标尺不能用来衡量文学作品,但是您在采访和创作时如何面对和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
杨显惠:有些作品中的人物名字和现实中是一样的,但绝大多数都换掉了。文学写作是要突破一切框架的,当你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衡量的标准,你怎么衡量,你就怎么来写这个东西,你不要管那些道德伦理的东西,你要按那些来写的话,什么真实就都出不来了,写不真实了。作家创作实际上是在表达对世界的看法,而不是固有的传统的看法。你必须与别人不同,所谓的与别人不同,不是你故意做作的,而是你的心灵就是这样。你要心灵非常自由,你如果心灵没有自由,你创作就没有意义。
张晓琴:情感与道德矛盾的典型例子是《李祥年的爱情故事》,李祥年与俞淑敏的爱情悲剧及其后的艰难“团圆”非常打动人,但是从道德方面来看很难让普通人接受。我有一个疑虑,就是您的采访对象,您作品中的人物原型是否乐意您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写出来后会不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杨显惠:咱们就谈这个李祥年,李祥年是真名,没有用化名,他自己跟我说,你一定要用我的真名。但是其中很多东西我都改变了,尽管我写的是他的生活,但在里面必须做很多改变,这就是虚构。比如说,李祥年的女朋友不是在石家庄,在另外一个地区,可是我把她写在石家庄了,我不能把他们的秘密暴露出去。
张晓琴:作品发表出版后会不会对李祥年本人产生负面影响?
杨显惠:没有。李祥年自己要求用他的真名。被采访者本人不说用真名的时候,我绝对不用他的真名。
张晓琴:您在采访中有没有遭遇过拒绝?

杨显惠:当然遇到过。比如说当年在夹边沟待过的有很多人还活着,我知道的是夹边沟有3000余人,活着出来的有500余人,在我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活着的还有一二百人,在我和他们接触的时候,有些人就坦坦荡荡讲述,有些人则不愿意,或者说干脆不见我。我在农场的时候认识一个知青,他后来调到武威当图书馆的副馆长。他看到兰州的《都市天地报》转载《上海文学》发表的《夹边沟记事》的时候,就对我说:“你不是调查夹边沟的事情吗,我的几个朋友是夹边沟待过的,你到武威来,我给你引荐他们。”我就从兰州坐车到武威,到朋友家,朋友去叫人,结果一个人都没有叫来。遭遇拒绝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也有的人见了却不愿谈,采访十个人,能够成功采访三个人就是最高的比例。
张晓琴:在您的采访过程中,最让您难忘的经历是什么?
杨老师:我最难忘的是为《定西孤儿院》做采访的时候,通渭县有一个妇女谈到她们家人饿死的过程,我忍不住了,说暂停暂停,咱们不要说了,我休息一下。我跑到外面站到院子里头哭去了。
张晓琴:您作品中对人性最残忍的书写就是“人相食”,也就是“吃人”,当然,这里的“吃人”与鲁迅所说的“吃人”还是有区别的,您作品中的人是在极端的饥饿状态下“吃人”,其中最残忍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母亲吃自己的孩子,这样的历史实在是让人不忍直视,您是如何面对这样一种极限的采访的?
杨显惠:我觉得我好像是专门为此而去的,所以我能够面对。
张晓琴:我想问一个更深入的问题,张纯如得忧郁症和结束自己的生命都与她调查南京大屠杀有关,书写人性失衡残忍血腥的历史的过程也是一个考验写作者内心是否强大的过程,您的著作,尤其是前两部,面对的是人性变形的历史,在极端的饥饿和政治磨难中,人往往失去了常性,显现出残忍、血腥、恶劣的一面,您采访并且把这样的历史和人性写出来时是否有强烈的愤怒和悲痛,这样的情绪时间久了对您本人的生活和心理有没有影响?
杨显惠:张纯如的东西我没读过,她精神出问题那是她自己太脆弱了。
张晓琴:您的采访与写作对您本人的生活和心理有没有影响?
杨显惠:写作是一个悲喜交加的过程。喜是我觉得我挖掘到了很深的东西,悲则是我们经历过的这种历史确实令人发指,你看到我写的不动声色,这其实是我的一种追求,我写作的过程就是一天到晚哭鼻子抹眼泪的过程。有时候我在我的书房里,我夫人在外面客厅里都听见我在哭呢。
张晓琴:您的部分采访对象是旁观者,他者,但是更多的采访对象是苦难的亲历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重述一次自己的苦难史是需要勇气的,同时也是灵魂的又一次考验,您在采访中有没有关怀安抚他们的灵魂?
杨显惠:能把自己的苦难讲出来的人都是很坚强的,这个时候去安慰他,我觉得是不合时宜的。
张晓琴:甘南有许多地方仍然保存了比较原始的文化和民间意识形态,但是一旦遭遇现代法律就立刻产生矛盾,显现出无力与脆弱。《甘南纪事》里还有一些读来令人心生难过的事情,比如不合恒常的道德标准的事情,当事人似乎也很无奈,但是只能接受,您在写作时是如何看待这些矛盾的?
杨显惠:有关这一点还可以写得更加深入,虽然我一直在考察甘南,但还是带着外来者的东西,我还在继续考察,还想更深入。
三、如何抵达真实及新的走向
张晓琴:您的创作被看作是跨文体创作,是什么促使您选择了这样一种文体?
杨显惠:选择这种文体,首先是因为我好多年都在写小说,尽管我写的很多都是真人真事,可是我把它写成小说的形式。小说是文学表达里边一种很好的方式,可以进行一定的虚构,某些东西我可以删掉,某些东西我可以加强,有些东西不够时我可以从别的地方拿来补充一点,我很喜欢小说写作。
张晓琴:您的作品虽然被看作非虚构的代表,但以我的阅读经验,您的作品恰恰是充满了虚构色彩的,文体和叙述方式的选择上都极为考究,“命运三部曲”中叙述视角各有不同,语言也各有千秋,您认为自己的创作到底是虚构还是非虚构?
杨显惠:我很感谢你说这样的话,有些人在读我作品的时候觉得是真实的素材打动了他们,实际上,我在写作时非常重视结构和语言。
张晓琴:您认为文学创作的本质是虚构还是非虚构?
杨显惠:这个问题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因为我写的很多是真事真人,只有局部的补充或者减弱,可是整体上来说,还是以真实为主的作品。
张晓琴:从这一点上说,文学究其本质而言意义何在?
杨显惠:文学的意义就是抵达真实。
张晓琴:事实上我一直也很关注这个问题,去年还写过一篇文章就叫《抵达真实之路》。我认为文学的本质是虚构。但是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最终目的就是抵达人类内心的真实。
杨显惠:即使虚构也必须写出一种真实的本质出来,文学的本质就是,你用写实的办法写出来,或者用虚幻的办法写出来,你终归要抵达真实。
张晓琴:“命运三部曲”的书名第一部用“记事”,后两部用“纪事”,您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
杨显惠:《夹边沟记事》特别讲究真实,我记的是真事,所以用言字旁的记。
张晓琴:记言立史。
杨显惠:到写作后两部书的时候,我就更讲究艺术,虚构的成分就有了。比较宽泛一些,不特别强调事件的真实性。这个时候,我就不用言字旁了,而是用绞丝旁。小说也可以叫做纪事,比如孙犁的《白洋淀纪事》。苏联一个大评论家办的杂志叫《祖国纪事》,里面有许多虚构的东西。
张晓琴:我觉得您的作品,好像表面看起来很纪实,实际上结构、叙述、语言都特别考究。我看到一个有趣的细节,您在《甘南纪事》一书提到最早去扎尕那是在《一条牛鼻绳》中,这篇开头中写您的经历是真的吗?还是虚构的呢?您把这篇放在了第三篇,而书中第一篇却写恩贝,第二篇写白玛,两个惊心动魄的复仇的故事,我相信这样的安排是有用意的,用意何在呢?
杨显惠:《一条牛鼻绳》的开头肯定是虚构的。至于排序方面倒没有特别动脑子,我认为第一篇的内容一下子要给人一种冲击力,当别人拿到一本书,一般都是从前边看起,第一篇就要把读者抓住,让读者一晚上把这本书读完,就是这样。
张晓琴:您的作品叙述视角都很丰富,《甘南纪事》尤其如此,里面有第一人称叙述(作者“我”),有第三人称叙述(比如《恩贝》、《白玛》中的讲述者达让),也有全知全能的叙述,各种叙述视角共同运用,又在随时转换,您在创作时是怎么考虑设置它们的呢?

杨显惠:两种原因,一是你不能给读者一种审美的疲劳,要不断变化;二是怎样才能讲好故事的考虑。同样的故事,哪种办法讲出来效果好就用哪种。
张晓琴:您的创作真正实践了文学的田野精神,完全不书斋化,在考察甘南之后,您的下一个考察目标是哪里呢?
杨显惠:下一个?(笑)我已经七十岁了,不会再开辟下一个战场。
张晓琴:您肯定还有许多采访的资料没有写出来,比如右派们平反后的人生,他们的未来;比如定西孤儿院中人物的更丰富的人生;比如甘南更多的人和事,您下一部要写的作品是什么呢?
杨显惠:今后的几年我准备先写完《甘南纪事》的续篇,再写上二十万字。素材都已经有了,需要再沉淀一下,明年开始动手写。我想真正进入藏族人的生活并且把它写下来。要深入。
张晓琴:《甘南纪事》里侧重藏民族在大的文化转型时代的文明隐痛,您在续篇中的侧重点会在哪个方面呢?
杨显惠:我会写的更深入。我举一个细节:我第一次去扎尕那是2006年,当时那里没有一个汉人。
张晓琴:我第一次去扎尕那也是2007年,当时甘南的朋友还指着一个村庄说:杨显惠先生最近一直住在那里。那时确实没有见到汉人。
杨显惠:可是今天扎尕那已经成了甘南的第一景点,游客量已经超过了拉卜楞寺。
张晓琴:游客们看到的只是大概,很难深入细部。
杨显惠:扎尕那有这样的小细节,《小妹的婚事》中的更堆群佩家里现在搞农家乐了。我对他说,让你爸爸洗洗澡。有些游客不在他家住的原因是更堆群佩的爸爸身上有味道。更堆群佩说让我劝,我也劝不了。年纪大一些的藏族人认为身上的垢甲越厚越好,这样人才活的长久。更堆群佩的爸爸老万考认为让他洗澡就是受罪。
张晓琴:这与《礼物》中他们家阿婆的保暖内裤的故事异曲同工。
杨显惠:我要写一篇关于这个老万考的故事。我第一次去扎尕那时住在他家,以后我每次去扎尕那至少要在他家住一晚上,我要不住,他就不高兴。他见我就说,你有新朋友啦,老朋友就忘掉啦!所以我到别人家住了以后呢,别人家房子即便空着,我也要跑到他家住一晚上。
张晓琴:您在他心中是重要的朋友。这种思维方式是典型的民间意识形态的表现,但这在现代文明进程中就变得脆弱,很容易受到伤害,《甘南纪事》中的甘南人正在经受文化隐痛。是否可以说您的创作在此发生了转变:由雕刻民族苦难转向揭示文化隐痛?而这一命题正是当下有良知的中国作家努力的方向。
杨显惠:可以如此理解。
张晓琴:杨老师,再次感谢您!期待您的《甘南纪事》续篇!

杨显惠,甘肃东乡人,毕业于甘肃师范大学(现西北师范大学)数学系。1988年入天津作家协会专职写作至今。曾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中国小说学会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上海文学》奖等。主要作品有《这一片大海滩》、《夹边沟记事》、《告别夹边沟》等书。《定西孤儿院纪事》、《夹边沟记事》、《甘南纪事》等。

张晓琴,现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三届客座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与重要作家作品研究。近年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小说评论》、《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当代作家评论》《文艺报》等刊物发表论文五十余篇。著作有《直抵存在之困》、《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等。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3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