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枫,出生于1952年,祖籍山东青岛,艺术学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现任甘肃省曲艺家协会顾问、甘肃省人口文化促进会理事。主要从事民族民间说唱艺术史论、民族民间舞蹈史论、民族民间音乐史论、民俗及民间宗教等方面的研究。
2004年荣获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艺术科学国家重点项目个人成果一等奖,2006年获得甘肃省艺术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2011年获得第二届中国曲艺高峰(柯桥)论坛优秀论文奖,2012年重点参与的《文化艺术资源数字化管理与实例分析》课题荣获第四届文化部创新奖等荣誉。主要论著有《中国曲艺志·甘肃卷》、《汉唐时期的甘肃曲艺》、《敦煌遗书中“变文”对甘肃民间说唱艺术的影响》、《甘肃民族民间舞蹈民俗考》、《“花儿”形态与民俗考》、《祭祀舞蹈“赤格尔咒乌”民俗考》、《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甘肃文化建设大事记》、《本土文化资源闪烁文化强省的新思维》、《甘肃太平鼓舞考》、《中华民国时期的甘肃曲艺》、《民间说唱艺术在特色文化大省的地位和社会作用》、《甘肃少数民族说唱艺术初探》等。
记者赶到徐枫先生家的楼下时,已入古稀之年的他拖着刚做完手术的病躯前来迎接记者,让记者感动不已。徐枫的书房并不大,里面摆满了各类文史志书籍,其中有两个“大部头”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一部是《中国戏曲志》,一部是《中国曲艺志》,其中的《甘肃卷》就出自他之手。他自豪地说,《中国戏曲志》的《甘肃卷》是我的父亲徐列参与主编的。他对我的影响很深,我们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他像个长辈跟晚辈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我的父亲徐列先生是戏曲评论家、曲艺评论家和新闻工作者。他在兰州解放的当天下午就接管了当时的《民国日报》,也就是现在的《甘肃日报》,可以说是兰州第一批新闻人。1963年,11岁的我第一次来到兰州,那时我父亲在省文化厅艺术处工作,他看戏时经常带着我,记得曾经在金兰剧院,也就是现在的东风剧院,我在父亲的带领下看了京剧大师梅兰芳的《穆桂英挂帅》,当时就被深深地吸引,冥冥之中觉得自己以后可能会从事与戏剧和曲艺相关的工作。
文革期间,徐枫在永登县插队。“在生产队里遇到了三位良师益友,他们有的教我历史,有的教我外语,还有的教我诗词歌赋,现在回忆起来,当年并不亚于上了个大学,至今我还很感激他们。”徐枫说:“插队完以后,我分别到县保卫科和文化馆工作了一段时间。等到真正搞创作,已经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我在甘肃省歌舞团曲艺队工作,那时已经进入改革初期,全国艺术家们被压抑的创作欲望都迸发出来,各种艺术形式百花争艳,因为平时喜欢专研戏剧和诗词,领导就将一个把曲剧剧本改成相声剧的任务给了我,当时我虽然觉得压力很大,但同时也觉得这是个锻炼和检验自己的好机会。在改编的过程,我虚心向各位专家学者请教,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并且在当时连续演了200多场,这次改编的成功鼓励了我想要创作原创作品的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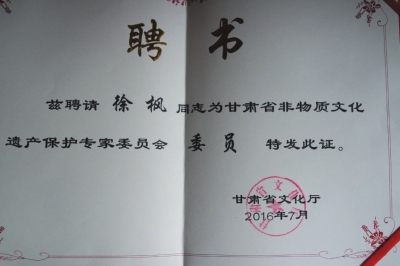
“就这么想着,机会就来了。”徐枫回忆说:“1987年9月,甘肃省文化厅突然招我去接受任务,让我赴湖南长沙参加《中国曲艺志》第一次编纂工作会议,其实那时的我仅仅是在甘肃省曲艺团工作而已,对甘肃的地方曲艺了解甚少,更谈不上什么熟悉。找我谈话的领导对我讲,‘文化部要编《曲艺志》了,甘肃不能落后。’就这样,我上了修志之船,开始了始料不及的修志航程。长沙会议是《中国曲艺志》的起航誓师,全国各地的修志人员汇聚一堂,令我瞠目。这里有一批很有学问的曲艺理论界的学者,也有曲艺表演界的名人。会上,随着《中国曲艺志·湖南卷》的编纂方案、《中国曲艺志·陕西卷》的框架本以及江苏、湖北、北京卷各编辑部的编纂规划展示让我有点吃不准,担心自己拿不下来,特别是《中国曲艺志》总编辑部制定的编辑体例以及编辑体例说明的报告更令我感到惶恐。随着会议的进程,最令我担心的是,什么是甘肃的曲艺,甘肃有哪些曲艺形式,这些都无据可查,一切都很茫然。”
就在徐枫颇为苦恼,一筹莫展时,他的父亲给了他极大地鼓励,让他坚持了下来。“他一直教导我做学问要扎下去,自己寻找材料,一切从头开始,才能将学问做扎实。”徐枫说:“让我没想到的是,编这部书花费了我20多年的时间。我学习到了以前从没有涉及到的学科领域的基础知识,曲艺涉及的学科太广,按志书体例的要求,我又涉猎了方志学、历史学、地理学、文献学、编辑学、民俗学、表演学、民族民间舞蹈学、戏曲学、考古学、宗教学等等,有一门搞不通,修志就无法进行。如果不去做大量的田野调查,不去做资料的原始积累,不去做民间人口的流向调查,不去做文献资料的落实,就无法掌握深藏于民间的艺术资源。经过20多年艰辛又美妙的钻研过程,我现在把甘肃民族民间说唱艺术的资源、民族民间舞蹈的资源,民族民间戏曲的资源、民族民间音乐的资源以及涉及这些领域的有关宗教、民俗、山川地貌已经深深地印在脑海里。也为我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回忆起撰书的艰辛过程,他回忆说:“二十多年的编撰过程让我理清了甘肃曲艺的脉络。为了搞清我省的各种曲艺形式和数量,我走遍了甘肃的85个县区、1000多村镇,走访了5500多位民间艺人和知情者,最后经查证我省土生土长的曲艺形式有78种之多,外来也有43种。”一边说着他一边熟练地打开电脑,给记者看了他悉心编辑的地方曲艺的目录,他按照曲种名称、形成期、主要曲调、流布地区和现状等方式分门别类地做以记录,如数家珍般一个一个跟记者说道,而记者看到在现状这一栏内,很多曲艺形式已经消亡。他极其惋惜地说:“从我整理的资料来看,几乎每十多年就有一个曲艺类型消失,这些承载着老祖宗文化与智慧的文化符号就像濒危物种一样慢慢不见了,它里面所承载和记录的文化内涵也随之消失了,它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没有可逆性,没有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记者问他我省的曲艺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期。他说,从唐代开始,我省就有明确的关于曲艺的记载。他在资料中翻出一句话来,“大中年间,沙州人创作《张议潮变文》”(变文,古代说唱文学体裁)”,这句话出自《敦煌遗书》。他说,别看就这么一句话,就花费了我一年的时间去考证。当年没有网络这么方便,要一本一本翻着查看,很多古体字也很难辨认,徐枫就将有用的资料和不认识的字一字一句地抄了下来。他一边翻阅资料一边感慨地说:“你说我们的曲艺历史有多深厚?马季的群口相声《五官争功》其实就借鉴了敦煌变文《燕子赋》和《百鸟鸣》,而《梁山伯与祝英台》也与我省的《百花楼记》如出一辙,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觉得甘肃省的曲艺资源太丰富了,真的需要好好去挖掘,不然实在太可惜,今年二月二我在永登苦水的庙会上,发现除了高高跷之外的其他更为罕见的膝跷和靴跷已经看不到了。面对这一现状我心里很着急,即使到了该享清闲的年纪,我还是放不下。”目前,徐枫编撰的《西北曲艺通史》和《甘肃民族民间舞蹈通史》已经截稿。
在多年的研究过程中,徐枫在民俗学方面的研究也很深入。他说,曲艺离不开民间音乐、风俗、宗教、原始崇拜,现在我们的优秀的民俗文化被西方文化冲击得有些不土不洋,其实我觉得好的民俗要保存下来。比如孩子们通过民俗了解做人的规矩,讲礼仪。好的婚俗让人们知道家庭和睦、尊老爱幼。传统文化就存在于这些富有生活气息的民俗活动中,我们不能把老祖宗留下的优良传统给弄丢了。

访问到最后,徐枫说:“在我看来,曲艺来自民间,用大白话说,就是老百姓自己说自己想说爱听的故事,既有国家大事又有家长里短,所以我的痛苦之处就是穷尽一生也无法把这一块做透。”回想起这么多年对甘肃曲艺的研究,徐枫的感情溢于言表:“我对甘肃民间曲艺的认识是在田野调查中逐渐形成的。在甘肃生活了几十年,真正对甘肃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丰厚认识是通过修志得来的,这种得来出于对民间艺术的尊重,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他说:“我不是什么所谓的专家,我只是一个热爱甘肃这块热土,喜欢这里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人。我爱甘肃已经超越了自己的家乡,因为甘肃的文化底蕴实在太深厚,我越研究越着迷,同时也隐隐忧虑,我希望通过自己做出的这些努力,能让甘肃的曲艺不至衰败,而是能保持,甚至蓬勃地发展下去。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3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