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灯长歌》:一部消失的泥土之歌,一部走向未来的大地之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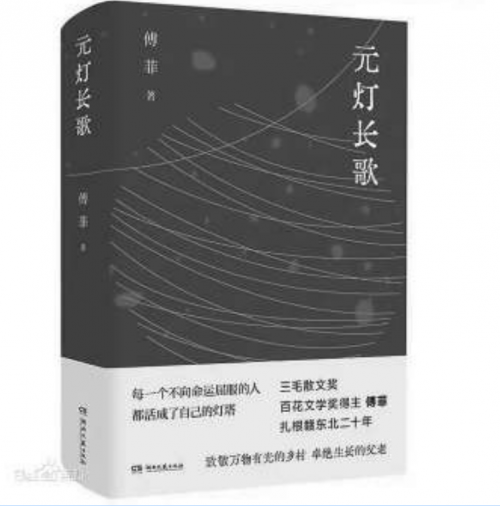
《元灯长歌》傅菲湖 南文艺出版社
读傅菲的散文《元灯长歌》,总使我想起另外一位散文家苇岸。“泥土就在我身旁”的苇岸,以乡土为对象,用质朴而简约的文字深情讴歌农业文明,表达着对乡土精神的眷恋;而傅菲更多时候对乡村的勘探,勘探地域文化、勘探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时的乡村现状、勘探乡村的生态伦理,他把乡村当作眺望这个世界的视角,渴望与之建立起特定的联系。
傅菲说:“我血液的上游,是一条河流的出生地。它是我观看、审视这个世界的坐标原点。”
某种意义上,傅菲始终还是个农人。他在寻找着土地的另一种未来:当传统乡村渐行渐远,在新时代乡村振兴大背景下,故乡是否能成为我们精神的原乡?傅菲给出了答案:
“我的双脚深深陷入土地,我的根须在土地下交错。我知道一粒谷种通往大米所走过的隐秘之路,正如一个家族枝开叶散。我和土地上的人血脉相连。土地是他们的证词,也是我的证词。”
或许,在傅菲看来,只有和土地建立隐秘联系的人,才能真正发现土地的未来。
一盏永不熄灭的故乡之灯
元灯是渊源、希望之灯,也是初始之灯;它是起点,也是终点。
元灯的故事是从死亡讲起的。弟弟的暴毙、妻子染疫而死、父亲故去……一系列惨痛事件拉开了大时代一位“纨绔子弟”的人生序幕。这个“纨绔子弟”叫傅元灯,他是傅菲的公(祖父)。当傅菲的太公傅文标用“元灯”这个词来命名他儿子时,寓意不言自明。
“我还是十几岁,公常常对我说:什么都可以丢,人不可以丢,什么都留不下,人要一代代留下去。”
坎坷的命运并没有击垮这位年轻人,他没有向命运低头,而是用不屈来抵抗着时代的洪流,一如余华《活着》里的那位“老福贵”。而后便有了姜桂生、姜荷荣等人的故事登场——
“姜村的姜桂生是一没落的大户之家,其妻月娥于晌午时分产下女婴。这是桂生的头胎孩子。女婴肥嘟嘟,面容肥阔皎白,啼声洪亮。”“姜氏家族有祠堂,有私塾。荷荣八岁读私塾,读了三年。十六岁,荷荣已出落得如荷花盛放,说亲的人络绎不绝……”
姜荷荣是傅元灯的第二任妻子,也是傅菲的嫲(祖母)。因丈夫意外离世,她改嫁到了傅家:
“1932年,姜荷荣自己挑着箩筐,颠着小脚,来到傅家。1935年秋天,土干气燥,荷荣生下一子,命中带土,兵荒马乱之年,取名土生。”
大概是“同病相怜”的缘故,傅姜二人就这样在枫林村抱团取暖过上了新生活。“2007年,是我公和我嫲的百年诞辰,家族有了大聚会。我公门下的血脉,百余人……”
随着时代的变迁、演进,傅元灯终于实现了当初的承诺——“人要一代代留下去。”而他们散落在历史尘烟里的往事,成了这座村庄里永不熄灭的灯,照亮着后人。“公嫲的墓地,在夏家墓的一个矮山冈上。公落棺之后,我再也没去过。但每年清明,我都要回枫林。我站在门口,远远地看那个荒草茂密的山冈。椭圆形的盆地,山冈贴着人烟,黑黛色的古城山像一堵高墙。太阳从山顶跳出来……元灯:渊源、希望之灯、初始之灯。我到了五十岁,才理解了这个名词。把它作为一个人的名字,是世间最好的名字了。我活在这盏灯下,如鱼活在饶北河里。”
那些消失的故乡人
傅菲不是一个简单的观察者或亲历者,他是枫林村的一分子,笔触所至,都自带温度——
“严春快六十岁了才第一次吃上樱桃。在种下樱桃之前,他还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叫樱桃的水果。樱桃甜中带酸,汁液丰沛,他爱吃。”
“墨离这个人,似乎从来不曾存在过,只有他的父母偶尔会想起,那个痴痴呆呆的儿子,去了哪里?是不是还活着?直到他的父母离世,也没再看过这个儿子。”
他以“在场者”身份呈现着自己所见所闻,如拍纪录片一般,还原着故乡里的那些手艺人、重症患者、鳏夫、离异者、嗜赌者、嗜酒者、创业者以及退伍军人的故事。他们不再被标签化,而是成为生活在我们身边活生生的“人”。傅菲通过他们与足下的土地建立起了血脉联系——
“我专注于着墨盆地人民的生存状态、内心困厄、精神风貌、时代变迁,以村志的形式,为河流立传,为大地塑像,为人民刻神……写他们与土地生死相依的高贵情感,写他们与命运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讴歌人性之美、劳动之美、伦理之美、生活之美、时代之美。”
在枫林村,傅菲是用赤子的情怀来书写这个村庄所发生的一切,追寻着生命存在的永恒困境。他在记录这些生命形态的同时,也目睹着他们的消逝。
散文集《元灯长歌》如同一部真实的社会纪录片,向我们展示着一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中的真实村庄现状:这里有贫穷、荒老和生存的挣扎;这里也有勤劳、狭隘和友善相伴。无论是远赴北京的林采薇,还是与村庄相羁绊的阿萝抑或是早已离世的小嫲……他们和脚下土地共同构筑起这个村庄的全部,成为村庄记忆的一部分。
元灯长歌,一部消失的泥土之歌,一部走向未来的大地之歌。(作者:黄涌)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3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