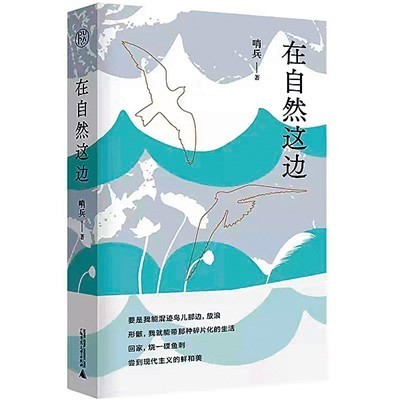
《自然课》《谈谈鸟儿》《青头鸭》《紫水鸡》《有关洪湖的野生动物及其他》……我猜测,诗人哨兵在《在自然这边》这本书写洪湖和自然的新诗集中“暗藏野心”:一种是博物志的野心,他充分利用自己对生活和自然的熟稔,为故乡真情抒写;一种是建立个人地域性标识的野心,他希望自己的写作能为这片土地确立属于它的文学位置;一种是“百科全书式”容量的野心,他试图将个人、自然、生活、历史、文化等尽可能多地纳入这本书中。更为可贵的还在于,他的这本书有重述自然、重铸诗歌的“自然”书写的野心,甚至可能是,先是有了这种追求,才有了这本《在自然这边》。
我如此猜度的根据,源于反复的阅读。在《在自然这边》的“自序”中,他略显急迫甚至带点小傲慢地向我们承认,他这部诗集,与“找到‘自然’,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传统有关”,与现代化进程中“自然”的变化和他对新诗可能的思考与探寻有关。是的,他试图接续传统,将属于现在、现实和当下的一切“纳入”自己的诗中,为其注入新颖、别致和统一性的诗意。
基于他的种种“野心”,使得《在自然这边》有一个整体性、总括性的思考,呈现的是一个“建筑群落”的面貌,而每一篇又能各美其美,显现异彩。诗集中的作品既有简洁的一面,又有浑浊的一面,既有单一向度的发力,又不乏繁复和深邃。在诗歌创作中,有“野心”是可贵的,更为可贵的是,诗人哨兵极有才华地实现了他的“野心”。
比如这首《向莲花及斑嘴鸭和护鸟人借宿》——
鸟儿让我哀恸。那只斑嘴鸭拖拽断翅
天黑时,又不知藏到哪里去了
躺在莲花底下时,护鸟人
绕着野荷荡,一直都在呼唤
那只鸟儿。这种声音
贴着洪湖传来,听起来
却来自世外,是虚无
在寻找虚无,空寂在寻找
空寂。躺在莲花底下后
每到护鸟人叫一下,斑嘴鸭
应一声,莲花就会落一瓣……
我认为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是,它描述自然和自然事物,但不是习惯性赞美和隐喻性抒怀,而是将审视、事实和个人悲悯强力接入。自然事物一方面依然是自然事物,另一方面,又变成了审视、想象、思考和追问的对象与载体,诗人在保护自然事物具体属性的同时又使它呈现为载体和容器,让二者相得益彰。第二,将叙事性纳入到自然书写中,在让它有了故事感的同时又凸显“我”的存在。“我”介入到自然和事件中,强化了个人性,也让“我”对自然事物更加“感同身受”。在中国诗歌传统中,自然要么是一种背景性存在,要么是造境中的“客观事物”,尽可能消弭个人的主观性,即使偶有强化也多止于“孤句”,是跳跃性的存在;而在哨兵这里,“我”的在场感和亲历性同时获得了强化。第三,悲悯性。我们以往的“自然”书写往往至“感怀”和“睹物思人”为止,但哨兵真正站在了自然的一边。那些自如的、自由的或是受伤的鸟兽虫鱼,诗人悲它们之悲、喜它们之喜、哀它们之哀、痛它们之痛……在这首《向莲花及斑嘴鸭和护鸟人借宿》中,哨兵的这一倾向显得足够清晰、真切。他将自己的悲悯注入受伤的斑嘴鸭身上,甚至让它的疼痛发出让人心碎的颤音:“每到护鸟人叫一下,斑嘴鸭/应一声,莲花就会落一瓣……”
我还将哨兵的这部诗集看作是对“洪湖”的一次次复写和复拓,他书写着洪湖的不同侧面、不同向度,在一次次的复写中,“洪湖”的水面被缓缓抬高,并且“生出”了涡流和浮游于水中的生物。每一首诗,是独立的结晶体,而如果将它们放在一起,便产生更为宏阔的统一感,呈现出在不断解读和抚摸中完整起来的“象身”,属于“洪湖”的——不,不只是属于洪湖的,它甚至令人惊艳地呈现了“百科全书”的性质,至少是一部区域史志。
诗人、小说家博尔赫斯有篇小说《创造者》,写一个野心勃勃的创造者,试图按照真实比例画下一幅世界地图。为此,他耗尽了一生的精力。而等他将这张“真实”的世界地图完成时,却惊讶地发现他画下的,竟是自己的那张脸。我一直将它看作是关于诗歌写作的经典隐喻,而在哨兵的诗集《在自然这边》中,我再次想到了它,因为它在某种意味上也是一种验证,验证哨兵在殚精竭虑的自然书写中,本质上画下的是自己的那张脸,是他个人精神向度的整体凸显。
阅读哨兵的《在自然这边》,我还发现其中一个极有意味的注入。譬如《古桑》《湖边休闲庄》《水雉》等诗,在并不刻意的自由联想中,我会想起《洪湖赤卫队》,那部有些淡忘了的电影中的歌曲。我当然能够意识到哨兵在诗中的牵挂,也能意识到,那样一种“境遇”为哨兵“成为自己”着色多多。我还发现,哨兵诗歌中某些词语的使用是“重”的,他有意强化语词的强度和张力,不肯略有平缓,而这些词往往又有种笃定的、斩钉截铁的性质。是故,阅读他的诗歌往往会遭遇小“颠簸”,它不肯顺滑而平庸,不肯像水一样倾泻着流淌,这是哨兵诗歌的个性之处,也是他诗歌的动人和耐人寻味之处。甚至可以说,他就是通过这样的“超过世界三倍重量”的诗句,为我们以为的熟悉重新命名,部分地,也建立起了深邃。
作者:李浩,系河北师大文学院教授、河北省作协副主席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3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