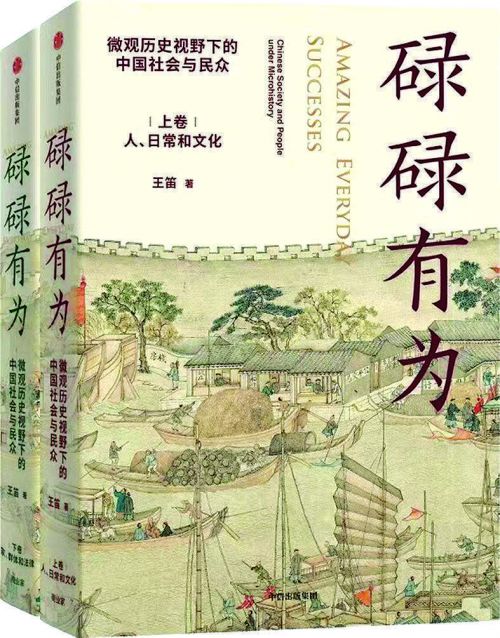
《碌碌有为: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 王笛著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1943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杨树因暑假到成都附近社会实习,在这里,她认识了40多岁的杜二嫂——一个以加工生丝、售卖丝绸谋生的底层农民家庭的主妇。次年,她完成了自己的本科毕业论文。半个多世纪后,杨树因的论文被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王笛发现,如获至宝,由此打开了一个通向微观历史世界的学术大门,至而“发掘”出大量充满浓厚民间地气的历史信息,并出版了《街头文化》《茶馆》《袍哥》《走进中国城市内部》《消失的古城》《那间街角的茶铺》等多部地气满满、脍炙人口的微观历史著作。
多年来,王笛一头扎进社会最底层,从人口的变迁、衣食住行、农村和城市的形成、秘密社会、风俗习惯、文人与教育、宗教信仰、法律与社会、宗族与家庭等多种维度,仔细打捞沉淀在民间的历史碎片,逐渐还原诸多历史细节。《碌碌有为: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共分上下两卷,上卷“人、日常和文化”聚焦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文化,下卷“家、群体和法律”则讲述家族、群体和法律。上卷更倾向于底层社会个体,下层则由底层个体逐渐向家庭、族群以及更大社会活动面发展,这也折射出王笛的历史研究视角,即历史不是少数个人的独角戏,同时也是下里巴人的叙事。
历史有时就是一开始的不经意,结果被大家仿而效之,久而久之便形成习俗沉淀下来。王笛经过梳理发现,今天国人对红木家具的膜拜,可能源自郑和下西洋返航用来压舱的红木。作为权力施加的对象,权力的一举一动,有时会成为下里巴人争相效仿的风向标。轿子原本是官员身份的象征,然而“先富起来”的商人纷纷模仿,终究遍地开花。“1916年,成都有490多家轿行,如果按每家10乘轿子算,总数也接近5000。”抬轿子的虽是下里巴人,但他们创造出“把乘客抬到屋檐一样高”让人惊恐的“拱杆”方式取乐,这无异于以肢体语言对双肩压力的一种戏谑式反叛。
王笛的写作带有强烈的问题导向,每一章前会提出一系列读者可能关心的问题,每章结尾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再梳理再总结,这种有始有终的写作方式常常能给读者以醍醐灌顶之感。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农业经济中心位于北方,后来之所以向南快速发展,王笛指出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大量引进的作物,更适应雨水充沛的南方;二是受北方边疆屡遭侵犯,百姓不得不一再南迁;三是唐代以后南方水利系统逐渐完善,困扰南方的水患问题得到较大程度解决。
农业离不开水,这也是农业生产中的一个突出矛盾。就这一问题,官府的解决方式有时简单得近乎残忍:“几百年前,山西的农民经常为水争斗。天越旱,斗得越厉害。后来官府以调解纠纷为由,在潭边支起一口滚沸的油锅,放入10枚铜钱,根据双方从锅中取出铜钱的数量,确定双方的分水量。”从散落在民间的一些地名,依然可以发现这样的历史脉络。
人口迁徙是中华文化交融的重要成因。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人口迁徙(安史之乱、永嘉之乱、靖康之乱)无一例外均因战乱。人口迁徙痕迹很容易从家谱中找到,比如湖广填四川后,许多移民自认祖籍湖北麻城“孝感乡”。查阅广东一些家谱和地方志,也可以看到许多族谱记载着其祖先是从南雄珠玑迁来的。
迁徙本身就是为了生存,为了生存,底层民众只能像成都的杜二嫂那样,在哪怕逼仄的空间里,也不放过一丝生存的希望。而“城市生活的繁荣依靠手艺人、小贩和商人”。川滇军阀在成都混战时,一旦战火稍有间竭,街头最早出现的必是小贩的叫卖声。商人的智慧总是超乎想象,“19世纪一位外国人在广州时,看到街道上门窗都是敞开的,屋檐都伸出一截。他同时比较了当时巴黎和广州的街道:在广州的街道上,商贩们本着对顾客充分信任的原则,将商品摆出来给顾客看,让顾客随便挑选,顾客们享受着充分选择的自由;而在伦敦或者巴黎的商店里,这是不太可能的”。遗憾的是,这样的商业精神并未能因势利导,发展壮大。
改革开放后,为什么浙江会率先成为民营企业的天堂?王笛从历史中觅得一些蛛丝马迹:“清代宁波城市居民中,有五分之四是劳动者和商人,其余五分之一为知识阶层;到了20世纪初,城区内30万人中,60%从事商业……可见,商业人口在城市市民中占比之大。”
传统习俗往往蕴含生存的智慧。民国有“正不娶,腊不订”的风俗。因为正月走亲访友很忙,而腊月里忙着准备春节,娶亲订婚这样的仪式只能在农闲时举行。然而同样出于现实需要,这些风俗早就改弦更张,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人员由于平时工作忙难以请假,反倒选择春节回家结婚,至于繁琐的“订婚”风俗则早就送进了历史的故纸堆。
透过王笛教授的文字,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历史既有山川大海,也有纵横阡陌,大人物的叙事无以取代下里巴人的命运悲欢。相较于上层社会经常遭遇的血雨腥风,底层社会的变化则要漫长得多,也细微得多,有的历经岁月淘洗,跨越时空,最终沉淀为公众喜闻乐见的习俗。从这层意义上讲,习俗又何异于一部活历史。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3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3